“宰白鸭”是啥?有一首诗就叫做《宰白鸭》,其创作者郭光启写到:“宰白鸭,鸭何辜?青霄在前面害怕呼。得钱效命代人死后,妄冀剖腹产可藏珠。”
这也是盛于清朝极端作风,地区官员官商勾结,纵然皇上一声令下严查,最终也没能避免。
“宰白鸭”层出不穷,昏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乃至参与进来。而廉官即便自知内幕,遇到这类冤假错案也无法改变,“宰白鸭”里的受害人往往会在去世后才来公平,或始终身负冤屈。
宰白鸭,鸭何辜
“宰白鸭”通俗来说便是凶手买进顶包,清朝光绪有一个有名的“王树汶案”,其受害人就犹如待宰的白鸭,没有抵抗力量,只有任由屠宰。

案子原因是一个离休官员被土匪打劫,他吞下不来那口郁气,因此气冲冲的去官衙报警。离休官员要在河南省抢不到,那时候河南省小偷猖狂,隔三差五就会有抢劫案件产生。但受害人并不是害怕被报仇而委屈求全,便是官员对此类案件置若罔闻,或贪污受贿匆匆审结。
由于本次报案者身份特殊,本地官员不敢懈怠,立即一声令下要抓捕小偷,因此出现了后面一连串的小故事。
只需确认了案发地点,实际上官衙要排查出凶手其实并不难,但是这个小偷真实身份不一般,其中又牵涉到官匪串通问题,因此案件一拖再拖。直至报案者自身探听到头目的名称,点名道姓要官衙捉人,官衙才迫不得已实施抓捕。

原来这个劫匪叫胡体安,而去掉劫匪这个称号,他仍然镇平县的捕头,因此他手底下有一些依靠他庇佑的马仔,那一天便是他的授意小兄弟来抢了报案者。
胡体安大白天用官方网真实身份耀武扬武,夜里则化身为劫匪四处打劫,过后滥用职权遮盖真实情况,确实要交叉的时候就掏钱买个穷光蛋来顶包。他这么依靠多重身份收敛性金钱,一直平平安安,让他愈来愈胆大心细,直到盯上此次的报案者。
一天,胡体安听闻来啦一个身有万贯家产的肥牛,他瞬间眼睛冒光,心头满脑就只有白花花的银子。
胡体安怕这一只肥牛被其他人快速解决,乃至赶不及多探听这人的来历,他便急急忙忙建立了打劫方案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胡体安多年来的捕头并没有白当,此次打劫他既没有行凶,都没致伤,按道理而言构不成死罪。因此胡体安手里拿着抢来的银两去洒脱,以为能和从前一样,最花大钱敷衍了事,过后他还可以继续做恶。
当知道报案者是离休官员后,他差点儿吓的脚软,因为这一次的危害过于极端,熟识律例他清晰死罪是躲不过的。
焦虑之后,胡体安又想要故技重演,可是这惹恼是指离休官员,有多少人喜欢做这一替罪羔羊呢?除非你是没有什么眼界,又很容易被唬住的无知少年。
正好胡体安家里有个才十五岁的佣人,名字叫做王树汶,没志气且没背景没事儿,是再好不过的替罪羔羊。胡体安寻得一线生机,随后巨资行贿前去追捕自已的衙役,串通一气唬王树汶,言而有信地确保但是坐两年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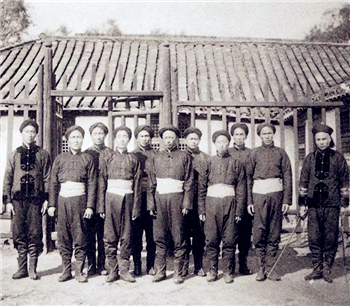
看他不愿意去,胡体安也是承诺为他益处,也是威胁他不在的话那就现场取过它的生命,吓的王树汶不反抗。
王树汶坐牢后,觉得落下帷幕的官员才对他说死罪这一事实。这消息如天崩地裂,再怯懦人在身亡眼前还会激发表现欲,王树汶当然现场改主意了,称自己是帮人顶包。
可不管她怎么伸冤,急切审结的县太爷都一口咬定这个人是凶手,使用严刑将其严刑逼供。上级领导官员也乐于前些完毕案件,也没有多多核查,即便摆明了王树汶与三十岁左右胡体安,在身型与年龄上面不匹配。
主动没有了活路的王树汶,泄愤的一般徒劳地高喊诬陷,一直到上去法场的警车,也大声伸冤,而恰好是这一举动将事情拥有转折。

王树汶高声自叙真实身份,控告自身遭到的不公工资待遇,在场的老百姓听到后纷纷猜测下去。她们尽管没有判案的能力,但都不瞎了眼睛,面前的青少年甚是柔弱,与身强体壮的小偷压根扯不上联系。
监刑官害怕忽视社会舆论将其斩头,因此赶忙汇报河南巡抚,王树汶得到临时捡回来一条命。
他碰巧来案子再审的好事,但是和这个案子相关联的官员怕丢失乌纱,抱成一团想将其推上去死罪台,持续往他的身上抹黑。要不是有要把本案严查到底的官员保他,他害怕是早已被灭口。
本来不会太难平反的冤狱,因为一众官员的相互之间袒护,活生生审了五年。直到王树汶刑满释放,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。

对于犯罪分子胡体安,早已改名来到别的地方消遥,到死都没绳之以法。而“王树汶案”只不过是“宰白鸭”中的一种典型性,有一些“白鸭”的冤假错案,在其中甚至还有至亲之人参与其中。
卖子求财运
清代陈其元撰写的《庸闲斋笔记》中,也是有相关“宰白鸭”史料记载:“商贾行凶,花高价给穷光蛋,代之情重,虽然有秉直之官,莫不受此迷惑,被称作‘宰白鸭’。”
书中有个有关“宰白鸭”故事,承担断案的官员并不是昏官,且了解“白鸭”的冤屈,最终却仍然判他死罪。这一官员不是外人,恰好是创作者的爸爸陈鳌。
陈鳌以前办理过一起打架导致死亡案件,逝者的身上伤口有十多处,很明显是被围殴。陈鳌刚想清查凶犯,想不到又有人来源于首了。

投案自首的是一个面色暗黄的十六岁少年,一看就并不是逝者的敌人,凭他本人根本无法击倒逝者,即使有参加打架,最多只是共同犯罪。
陈鳌按程序喊他阐述犯罪行为,他说道得与评审的笔录一字不差,那个样子并不像一个犯人在自叙,更像是在记诵提前备好的言论。陈鳌心里一目了然,这少年是帮人顶包来啦,凶手另有其人。
但是他再三审讯,青少年都会说便是凶犯。陈鳌于事无补,只有先把他当成凶犯在押候审。
其实她如果糊涂一点,沿着凶手的意将青少年斩头,他得贡献又无后顾之忧。但陈鳌不是这种能草芥人命,还可以坦然接纳奖赏的昏官,它的良知不可以他草率审结。那么想要救这个男孩,除开捉到凶手外,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翻案。

陈鳌赶到拘押一个少年监狱前,看他蜷缩在监狱一角,搞清楚他仍然畏惧砍头的,并不是毫无求生念头。毅然决然要救他一命陈鳌,晓之以理动之以情,溜了好几趟才使得青少年松嘴,亲自讲出自己是个帮人顶包。
但陈鳌未能提出这个人是替谁顶包,但是这并不奇怪。青少年或许是害怕被报仇才不会说,又或许他是真的不知道谁买自己的生命,终究凶犯不一定会亲自出面,反而是授权委托能办到这事的人。
青少年翻案后,这案件驳回再审,如果不出意外需要被无罪判决。陈鳌觉得做了一件好事,却没想到他再次见到他。
这时的青少年与以往有点不一样,他神色发麻,眼里已经没有了求生信念。陈鳌十分疑惑,问为什么再度翻案,青少年潸然泪下,把自己的遭受跟他说了。

她在牢中苦干时,它的父母曾来探视,她们看他安全,却没有一丝欣喜的模样,反倒像见到仇敌一样,对她痛骂道:“卖这个钱已耗尽,而你却翻案,你重要父母吗?假如你刑满释放,揍你!”
也有县上被收购的官员私底下对她使用严刑,逼着他承认自己是真凶,青少年遭到心身多重打击。他想要连父母都恨不得他前些被斩头,他就千辛万苦承受这痛不欲生的日子干什么,比不上投案自首少受些苦。如此一来自己可以获得摆脱,又顺了父母的意,当她尽到了最后孝。
陈鳌才得知,青少年并非自行变成“白鸭”,而是将父母卖给真凶偿命。陈鳌对于他的遭受倍感悲痛,他意想不到天底下会有这么绝情的父母,居然亲自推自己的儿子进火堆,使用了他效命钱父母或许这才是最不想让他生得人。

此次青少年铁了心要顶包,不管陈鳌怎么劝说也不愿意翻案,即便清晰他可怜,陈鳌也只能是忍痛割爱判他死罪。这把大砍刀斩的不仅仅是青少年的头颅,更加是陈鳌这颗仁义之心。
办好这个案件后,陈鳌对污秽的朝中非常失望,给自己乏力还受害人清正而惭愧,竟然脱掉一身正版手游,自请弃官。
难道是皇上对“宰白鸭”浑然不知,才会导致“宰白鸭”冤假错案高发吗?其实也不是,事实上曾经有高官因“宰白鸭”所以被皇上杀一儆百,皇上更加是一声令下严查过这类事件,但是效果微乎及微。
盛行根本原因
早就在乾隆在位时,他便曾将一个导致冤假错案的大臣怒降三级,期待别的高官以此为戒。但到了条光继位后,“宰白鸭”风气依然风靡。

据史料记载,条光二年,仅是一个潮州府就查出来三十七起“宰白鸭”案。像“王树汶案”,这个案子在审结前也就成了全国名案,条光因此曾火冒三丈。但是,消息之后一切故伎重演,地方官员只懂得将消息捂得更紧。
实际上“宰白鸭”并非清代独有,往往他会清朝盛行,是因为它时代特征与法律漏洞给了它滋生蔓延室内空间。“宰白鸭”在乾隆皇帝以后迅速发展至顶峰,其实就是执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后。
闭关自守给清代所带来的大于利,不仅阻拦社会经济发展,还推动了清代体制的奔溃。长时间不与外界接触,使清王朝失去生命力,随之而来的是浑浑暮气,腐坏一寸寸吞食清王朝。
历代王朝几乎没法杜绝腐败风气,很难做到无一桩冤假错案,而往往有与其斗争的一股廉明风气存有。二者并不是旗鼓相当,便是今天我压我一头,明天我胜你一招。

而到清朝晚期,廉官宝贵,更重要的是无所作为的昏官。且就出现了地区与中央斗争的状况,强龙压但是地痞流氓,地区存想着隐瞒的事,中间听不见一点儿消息。这就导致地区的百姓想传递真正心里话给中间,越来越难于登天,只有任凭当地政府忽悠。
地区豪绅运用钱财打通关系,只要没有冒犯了不敢惹得人,仅用往官衙送银两,就一切都可搞定。即便是犯下死罪,先到极其缺钱花平民家中挑本人,再为高官送一份薄礼,真凶只要消遥,大砍刀怎样也落不上他头顶。
一些穷到吃糠咽菜的平民,为了能一家老小不会被饿死了,乃至自行成为他们的替罪羊,一手交钱,一手交命。替罪羊仅需盯紧自己是个凶犯,就能做到代替真凶,充分体现了清代政策制度的一大系统漏洞。

有别于当代注重直接证据,清代审理案件:“一经认实,即为了能事,到底所捐献者是不是可靠,不暇问亦不愿问也。”即使嫌犯显著与推断的真凶品牌形象不符合,高官还可以光凭笔录将嫌犯判罪。
这个漏洞更是给“宰白鸭”大开绿灯,真凶根本不用用心编造直接证据,只需让替罪羊背下来口供,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。
替罪羊一家都期盼着这效命钱救人,更何况能同意这件事情家庭绝对不会过后去闹,反而是闷声发大财生活下去,害怕这个钱也会引起买家的关注,招来多的是不便。
但是像陈鳌那般的廉官,纵然对内幕心照不宣,异常犯与笔录摆在面前,她们能做的事情竟然仅有相互配合真凶,将手中的笔变成大刀,将自己一想着维护的无辜的人置之死地。

长此以往,在各级就会形成极端作风,贪官污吏与官匪串通变成在所难免,官商勾结问题更为比较严重。老百姓有冤无从喊,逐渐可能就没有感觉了。
中间能看到的就是地区细心装饰完的,却不知自身眼里百姓安居乐业的区域,事实上早已被昏官们弄得人心惶惶。
如王树汶那样九死一生,好好活着来公道的“白鸭”寥寥无几,像那个少年一样冤死的才算是大部分。直到清帝退位,伴随着地痞流氓的消失,“宰白鸭”风气才渐渐消失。
可是这尽管已经成为过去,但并不是说它将被遗弃,还有很多未沉冤昭雪的冤假错案,“白鸭”的怨魂不可长眠。他的不幸遭遇,是对后世的警觉,坚信没有人可以期待重蹈覆辙,想要自身被迫成为“白鸭”。
由来:回放古往今来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